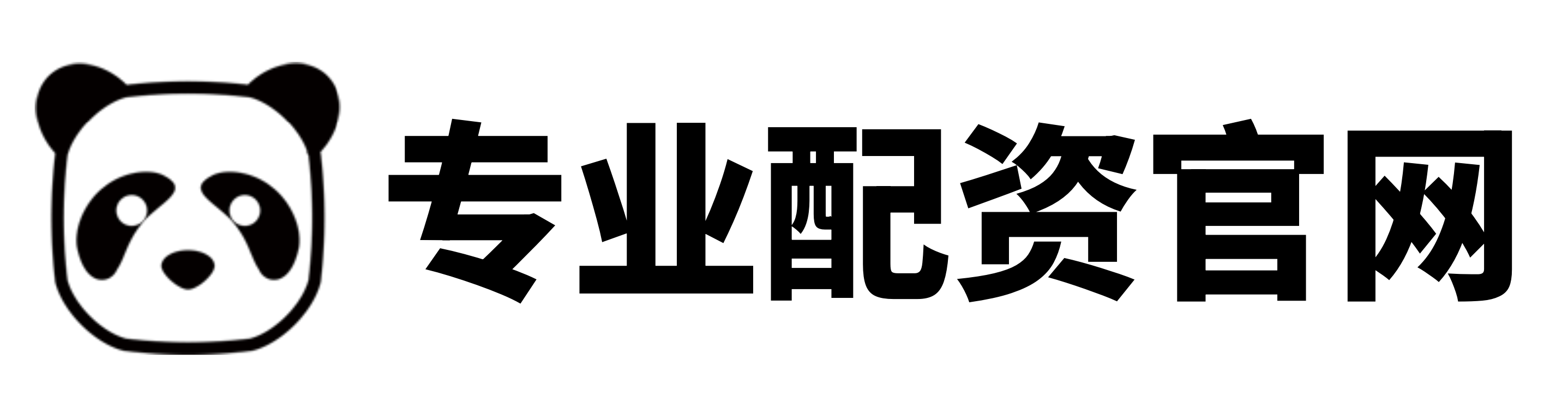股票策略网站 1949年毛主席召见傅作义,闲聊中问及:你这个部长是不是没权啊?

“(1950年2月下旬,北京中南海)主席,水利部的报告到了。”值班秘书端着文件站在门口。毛泽东放下烟卷,随口一句:“咦股票策略网站,还是副部长签的,你们部长是不是没权啊?”一句半真半戏的问话,把半年前的一段往事瞬间拉回众人眼前。

1949年2月,西柏坡夜色深沉,山风裹着料峭寒意。傅作义第一次踏进中共中央驻地时,没有想到自己昔日的对手竟会如此平和地对待他。房门刚掩上,他就低声说:“我有罪。”毛泽东摆手:“北平完好交出来,你可立了大功。”语气轻,可分量重。那天夜里,双方谈到天快亮,一笔笔算清了北平的和平得失,也为傅作义之后的去向定了调——军事委员会委员,再加一个水利部长的任命。
时间往前推半个月,北平城外的积雪尚未消融。起义部队整编、接管事宜千头万绪,傅作义忙得脚不着地。有人劝他:“反正职位到手,少出面多安全。”他只摇头:“城是我交的,人还得我来安。”这一态度,很快传到西柏坡,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宣布水利部长人选,以示信任。

其实,傅作义与治水结缘并非偶然。早在抗战期间,河套灌渠建设全靠他一锹一铲地推。十万官兵白天修渠、夜里打仗,硬是在荒沙滩上凿出数百公里水网。多年后他说:“战火也要吃饭,治水不耽误抗日。”这句话,当时许多人只当口号听,直到新中国缺粮、缺水的现实横在眼前,才明白那是经验。
然而,部长的红头文件刚印好,一股“倒傅”暗流已在部里涌动。几名老干部心里不是滋味——打江山时流血流汗,如今却让一个国民党旧将当家?于是能拖就拖,能卡就卡。一个月下来,水利部呈交国务院的公文,全是副部长的签名。毛泽东察觉异常,才有了开头那句“你这个部长是不是没权”。

事情挑明后,周恩来出面召集部门骨干,话语不重,却句句带火:“北平二十万守军无条件撤城,是哪位同志做得到?如果没有傅作义,你我今日坐在哪里办公,都难说。”会议不到半小时,所有人心中那点不平衡被戳得粉碎,“文件不经傅部长签字一律无效”的规定现场通过,再没人吭声。
权力障碍扫清,傅作义把全部精力砸进了河流勘测和灌溉规划。白山黑水零下三十度,他穿着棉大衣蹲在冰面画草图;珠江三角洲烈日暴晒,他提着测量仪一步步丈量潮位。同行的年轻技术员喊苦,他却笑:“修水利和打仗差不多,怕热怕冷不行。”这种不要命的拼劲,让很多工程提前完工,也让他的胃病和心脏病越拖越重。

1957年,引黄济卫工程进入关键期。傅作义顶着高烧从郑州赶到黄河大堤,刚一下车就扑通跪在土里掏泥样。随行医生急了:“部长,先吃药!”他摆手:“让河堤先吃药。”一句俏皮话,引得工人们哄笑,可没人敢偷懒——老部长都这样拼,谁好意思怠工?
有意思的是,外国专家来华考察,对着卷宗问:“这位傅部长是工程师出身吗?”翻译笑答:“不是,前半生当过军长。”专家难以置信。傅作义听后拍拍胸脯:“打仗的经验正合适,黄河脾气比敌军还倔。”

1960年代,全国水利布局初具雏形,他在《人民中国》杂志连发两文,总结“先蓄后灌、因地分段”的思路,成为后续治理黄河的重要参考。毛泽东看完批注:“懂行,钻进去了。”短短四字,是对这位旧将的最高评价。
时钟拨到1974年春。那年京城干燥,北方多地连月无雨。傅作义在病床上听完工作汇报,艰难抬手:“河北降水还是零?”护士含泪点头。他苦笑:“我活着就想着这点事,真不争气。” 4月19日凌晨,他停止呼吸,年七十有七。讣告中一句话格外醒目——“毕生献身水利”。

纵观其行迹,傅作义曾两次站在人生十字路口:一次在平津战略决策,一次在新中国治水蓝图。前一回,他保全了古都;后一回,他换来了沃野。路线抉择各有利弊,可落脚点始终是“国家和百姓”。这大概也是毛泽东敢于一句玩笑试探,一个指令维护的原因:功过往事皆可商榷,唯独这份担当,不容抹杀。
涨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